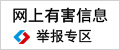離人散記
聶紺弩
在死傷、損失、焦土,這些字樣里,我仿佛看見了一些熟識的人們的血肉模糊的肢體,而最熟識的是不到兩歲的我的孩子和她的母親!
一天,我到朋友平羽的住處,時間已是晚飯過后了;意思是想和他散散步,談談天,趕走一天工作的疲勞。他不在家。我獨自坐在那整潔的像女孩子的閨房一樣的臥室等他回來。晚風飐動著窗簾,楓樹的落葉,飛進窗前的書案上;窗外的遠山帶著幾分褚色,在漸漸昏暗下來的天空底下,已經望不出顯明的輪廓。屋子里更是一片昏茫,只看見一張白紙在壁上飄動,那是我偶然寫的兩句古人的話:“但愿人長久… … ”被平羽貼起來的。
點燈的時候,主人回來了。神色似乎很倉忙,一面解皮帶,把腰里的短槍掛到壁上,一面問我:
“你不是京山人么?”接著:“你們家里被炸了!”
“哦!”我吃驚地問:“哪里來的消息?”
“廣播,剛才從參謀處聽來的。炸得很兇!”
我好半天沒有講話。臨走的時候,有氣無力地說:“你不該把這消息告訴我!”
晚上,在床上翻來覆去了好半天,好些時不曾到夢里來的我的女人和孩子,和我糾纏了一整夜。睡醒了,起床號的余音還在繚繞,晨光從窗外闖進。睜眼望了好一會,幾乎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。

油印的廣播消息:“五十余架寇機…… 死傷千余人,損失 …… 城內外盡成焦土……”
這很出乎我的意外,我從來沒有想到故鄉的天空五十幾架飛機的翱翔,也沒有想到竟有一千多人可供死傷,更沒有想到有將近百萬的財富。我在那偏僻的山城里生活過二十年,總覺得那地方只有一巴掌大,只有幾十家人家,三兩百人口,而且那是一些怎樣襤褸的人們啰!
在死傷,損失,焦土,這些字樣里,我仿佛看見了一些熟識的人們的血肉模糊的肢體,而最熟識的是不到兩歲的我的孩子和她的母親!
我沒有看見過炸彈炸死人,也沒有被飛機在頭上追逼得無路可走。碰見過許多次空襲,每次,被轟炸的地方都和我隔得相當遠,頂多只覺得墻壁似乎要移動和窗戶的震顫罷了。那末,五十幾架飛機在一巴掌大的地方盤旋的時候,那飛機底下的人們的心情是怎樣的呢?五十幾架飛機在比屋脊高不了幾尺的天空,一齊吼叫著,那是那山城里曠古未有的死神的怒吼吧!是不是只聽聽那吼聲,就可以使人亡魂喪膽呢?
我不能想象!五十幾架飛機上的機關槍向地面掃射著,五十幾架飛機上的炸彈在地面上爆炸著,那是怎樣一種天崩地塌的聲音啰!只是那聲音,不就可以使人震破耳膜,迸出眼珠,爆裂血管么?我不能想象!五十幾架飛機可以把那巴掌大的山城完全翻轉來,可以使那城內城外的每一個人,每一只狗,每一個螞蟻甚至每一只烏鴉都會感到上天無路,入地無門吧!那時候還有什么守財奴貪戀他的財產,還有什么暴君會虐待他的奴仆,還有什么債主拉著欠債人不放或地主逼住佃戶討租呢?就是獅子也會不對獐兔之類垂涎,而貓卻和老鼠擁抱在一塊兒抖索的吧!
這是怎樣巨大的一個戰栗喲,但是我不能想象!在飛機剛剛飛到的時候,有多少人在那窄狹的街道上奔跑呢?多少人在號哭,喊叫,兒女,爺娘,丈夫,妻子… … 誰也顧不了誰,誰也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的好;老弱的人在人潮里被擠倒了,也沒有人扶起的吧!雖然有嬰兒在腳底下,也會踏過去的吧!我不能想象!
我想象飛機還沒有到的時候,那城內城外的人們不還是和平常一樣,甚至和沒有打仗的時候一樣地過著日子么?西城外的鬧市還是那樣擁擠,文廟里還是社訓隊在那里上操,十字街的面館還是賣著熱氣蒸騰的點心,完差的鄉下人還是背著褡褳向衙門里跑。
……那古老的城墻還是像荒古的爬蟲,靜靜地偃臥著;城隍廟里的神像仍舊金碧輝煌,廟對門的塔,塔頂上的老鴉窠,窠里的老鴉還是飛去飛回,一天到晚地忙著。
…… 我家的大門口有一塊有凹的紅石頭,那凹,恰像一個腳印,我小的時候,常常踏在它上頭好玩;我這回離家的時候,它仍舊在那兒,自然也仍舊放著紅光。我那矮塌的,窄狹的房子,仍舊像什么時候都要倒下來。那房子里的主婦,每天清早要帶著被窩,爬在床邊,端她孩子的大便;那孩子手里拿著一塊餅干什么的,口里唱著連自己也不懂的簡單的歌,耳朵里聽著媽媽的哄騙,行若無事地排泄著那小身體里頭所不需要的東西,那墻上掛著孩子周歲的放大照像,小柜上擺著孩子的食品、玩具和藥物,這時候都會很快樂似地和這母女兩人打招呼;只有那書架上新由朋友贈送的一部大書《說文詁林》倨傲地躲在那里,從來也不理人!以后是女傭人倒水進來,主婦起來,到學校里去和一群頭上生著癩痢,嘴邊掛著鼻涕的孩子們周旋一個上午;回來的時候不是到婦訓班就是到婦抗會去看有什么事情,路上如果碰見郵差時就問一聲:“有我的信么?”她差不多每天都盼望從江南寄回的家書。縱然在戰時吧!這也是一種恬靜的生活,卻并不是游惰的生活呀!誰會想到一兩個鐘頭以后,半個鐘頭以后,甚至一刻鐘,十分鐘以后,就是自己和全城的毀滅呢!
然而飛機來了!一來就是五十幾架!當然啰,什么都完了!那城墻,那廟宇,那塔,那塔上的老鴉窠,門口有凹的石頭,那住了幾代人的房子,房子里孩子的照片,小柜,柜上的瓶瓶罐罐,書架,架上的《說文詁林》,尤其是房子里的主婦,孩子,女傭人,都和全城內外的人和物遭受了同一的劫運!炸彈沒有炸死的,機關槍會射死,機關槍不曾射死的,會有倒塌的房屋壓死;壓不死會被磚頭瓦塊打死,火燒死,火藥氣味薰死,激烈的響聲震死;再不,就在人叢里擠死,跌死……總之,完了!什么都完了!我恍惚看見了死神的笑;看見五十幾架大獲全勝的日本飛機排成一列悠長的隊伍,在天空得意地低昂,舞蹈!還恍惚看見那事后的廢墟上裊著一縷縷的殘煙剩火,甚至有一兩個幸免的人,像做夢似地從斷瓦頹垣,尸山血海中探出頭來,一面還摸著自己的脖子。
天哪,這是真的么?這簡單的廣播,傳給我的是這樣一個消息么?
這是真的么?那全城的人,男女老少,我的親戚,朋友,熟人,都完了么?那些人們,有許多我曾經厭惡過,憎恨過,愚昧的臉,狡猾的眼睛,骯臟的身體,頑固的心……然而現在想起,他們是多么可愛呀!他們才真是一些無辜的純良的人咧!
這是真的么?我的愛人,我的妻子,我的最好的朋友和同志,那和我在一塊兒生活了十幾年,共同開辟了自己的道路,共同嘗過了生的歡欣和苦難的人,那唯一能夠理解我,信任我,督促我,鼓勵我,而又原宥我,撫愛我的人,那像一盞綠燈一樣,在人生的血海里照耀著我,召引著我的人,竟連“再會”也來不及向我說一聲,訣別的淚也沒有流一滴,就帶著她的孩子去了么?
我的一歲半的孩子,再不指那餅干盒了要東西吃了么?每天早上再不和屋檐上的麻雀一道兒吱吱呀呀地叫了么?她那細小的骨頭,柔嫩的肉,那無邪的,一片天機的姿態,都做了死神的“牙祭”么?戰爭一開始,她的媽媽就和她的爸爸商量:這偉大的戰爭必須耗去無數的生命.我們活過幾十年,喜怒哀樂都受夠了,就是死也沒有什么遺憾;但是這孩子還只剛剛出世,完全不知道人生是什么;她需要活著,應該活著,至少我們中間應該有一個人為她而活著。戰后的中國將是個新的社會,而她們將來是新社會的主人;如果不為后一代人的幸福,這戰爭的內容就會貧乏得多的吧!不錯,她的媽媽和爸爸,現在還有一個人活著,可是她自己卻沒有了!那無助的小生命惹過誰呢?犯過什么罪呢?我向遙遠的天邊發出這倔強的疑問。
我不是什么英雄,也不是什么志士,至少我的感情不是的;我是一個人,一個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人。我愛我的妻子,愛我的孩子,愛我和我的妻子、孩子構成的家。我愿意幸福,愿意我的妻子,我的孩子,我的家幸福。我還只三十幾歲,應該還有幾十年好活;我的妻子比我的年紀小,孩子自然更小;我不愿意她們在我之前死去。尤其是孩子,我要好好地讓她長大,好好地教養她,讓她長得像一朵花一樣;讓她的性格,知識,思想,能力,就是在未來的她們的社會里,也像一朵花一樣。我知道,這多少是一些幻想而且很自私的。但這幻想,這自私,卻正是我的心靈的實有物!中國有多少像我這樣平凡的人,有多少這樣的自私的幻想呀!故鄉,那古老的城里的人們,我熟識他們,理解他們,他們全和我一樣,我幾乎可以一個個地數出來!可是現在那殘酷的魔手給我們把這些東西一齊毀掉了!
大概過了一個多月吧,我的心像橡皮什么的一樣,什么感覺也沒有,也不知道日子是怎樣過去的。在這時間中,也許我快活過吧,也許笑過吧,假如有,那是怎樣快活起來的,怎么笑起來的呢?連我自己也不理解。
怪不怪,我怎樣也沒有想到她們還活著。那怎么能夠呢,五十幾架飛機,一巴掌大的地方!
多意外呀!我接到一封信,一看封面正是我所懷念的人的筆跡,再看郵戳,是被轟炸以后的日子,我簡直不能說出這是怎樣的一種狂喜!親愛的讀者喲!請原宥我的筆,寫不慣幸福和歡快的感情!總之那緊繃著的心一下子就松散下來了。
那信是告訴我被轟炸的消息,轟炸時候的情形,大致是那油印的廣播消息的重復。她說,除了城墻還有剩下的以外,就都是一片焦土了,另外還說誰死了,誰受了傷,誰的太太,誰的孩子……大串熟識的人名。在這兒出現名字的人,縱然還是活著,也多少有些不幸的事情,至于我們家里呢?房子倒完了,不必說:僥幸人都好好的。孩子已懂得飛機這兩個字,一有人提起,就不哭不鬧,兩手抓住媽媽,小頭緊緊地貼在媽媽懷里。
信的末尾,她還發了一通議論;因為是寫給我的信,議論很簡單,如果鋪張起來,應該是這樣:
日本的空軍是英勇的,它能使我們的一歲半的孩子害怕,能夠使這沒有任何防空設備的小城變成焦土,能夠使一些沒有地方躲避的人們死傷之后,還能夠除了炸彈,除了機關槍彈,除了汽油以外,沒有任何損失,假如“凱旋”的歸途不碰見我們的空軍的話。
可是為什么只來五十幾架呢?不是就是來五千架,五萬架也仍舊可以毫無損失,一架不少地回去的么?為什么還讓剩下一些城墻剩下一些人呢?不是就是把地殼炸穿了,叫螞蟻、臭蟲,無論什么生命都絕種了,底下也沒有人會放一個炮仗的么?多么好大逞雄威的機會呀,這才真是“無敵”咧!
不過你要知道:日本皇軍怕咱們中國人沒有敵愾心,拚命地制造,煽發!不是還剩下許多人么?他們和以往不同了,茍安的,僥幸的,畏縮的,以為鬼子來了只要當順民就可以太平無事的心理不知到哪里去了!沒有人不想吃鬼子的肉,喝鬼子的血。他們已經沒有家,沒有產業,沒有掛欠,就是生命也像是拾來的一樣,還留戀什么,顧慮什么呢?以前無論怎樣聲嘶力竭地對他們講,許多人的回答是懷疑的眼光,那樣子叫人擔心鬼子真地會來。現在呢,沒有一個人還需要宣傳。他們什么都懂,每個人即使最笨拙的都可以自己當宣傳員。… … 說起來真慚愧呀!這是鬼子的功勞,而且花的代價太大了!
可是她的議論并沒有在我的腦筋里引起什么反應,我已被快慰的情緒弄得不能喘氣了,為了她們的活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