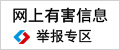——回憶我的寫稿生涯
1965年秋初中畢業至1980年秋,回鄉務農15年,也是我從事業余寫稿的15年。鋤頭是筆,在大地這張厚紙上書寫著農人的春夏秋冬;筆頭為犁,在一張張薄紙上深耕著一個年輕的夢想。
頭5年,生產隊還沒有推廣種植雙季稻,比較閑散,基本不出夜工。白天勞動,夜晚便由我自由支配了。夜晚點燈費油,天一黑人們就睡了,而我為了擺脫這種“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”的農村生活,就在夜晚拼命地讀書和寫作,決心從寫作中殺出一條血路來。
那時節,集體和個人都很窮,家家戶戶照明都是隊里分的幾分錢一斤的柴油,煙子大,光線差。我點的煤油罩子燈,玻璃罩著,煙子小,光線明亮。煤油是三角六分一斤,在供銷社打的,稱之為“洋油”,農村人認為點煤油是侈奢浪費。剛一下學,在外地行醫的父親就叫他的徒弟、石廟公社衛生所所長江作新叔叔給我送來了一本中醫啟蒙書《藥性賦》,要我學醫,說,秀才學醫,如籠里捉雞。我對學醫當醫生不感興趣,這本醫書我基本上沒翻,覺得枯燥無味,母親就叫妹妹監督我。
每到夜晚,我呆在我家雞籠旁邊只有一桌一椅一床的小屋子里看小說,學習寫作技巧。只要一聽到妹妹的腳步聲,我就拿著那本《藥性賦》,搖頭晃腦、抑揚頓挫地高聲朗讀起來:“聞之菊花能明目而清頭風;射干療咽閉而清癰毒;薏苡理腳氣而除風濕;藕節消瘀血而止吐衄……”妹妹一聽,車轉身向母親報告:“姆媽,哥哥他在看藥書。”母親說:“好,看藥書就讓他看,要是看閑書就把他的燈端起走,別糟塌燈油!”妹妹一離開,我又把醫書扔到一邊,繼續看小說或寫作,這完全是一種“地下工作”。讀初中時,父親給我的零用錢全都買了書,畢業回鄉時,挑了一大箱子書,夜夜都有書看,后來被紅衛兵抄家全都抄走了,很可惜。
我從事寫作,因為怕文章不被采用,逗人好笑,所以偷偷摸摸地寫,偷偷摸摸地寄。一次,宋河郵電支局一位30來歲叫蔡祥禮的鄉郵員(洪湖縣人)給我們大隊送郵件時,見我在投寄稿件,便告訴我,投稿信件不必貼郵票(因為報社是郵資總付),把信封剪一個小角就行了,新聞稿件必須要蓋公章。原來他也是黨報的通訊員,真沒想到眼下這位皮膚曬得黝黑發亮,每天騎著自行車跑村串戶的郵遞員竟然還是個寫作高手!
行話說,七分采、三分寫。寫稿容易,找新聞素材就難了。新聞又不能像文學作品那樣編造,而寫的是新近發生的事實,必須要何時何地何事何因何人五要素齊全,還要有新聞價值。而我一年上頭呆在生產隊出工,趕個集都還跟隊長請假,隊長不批就乖乖地出工,根本就沒有外出采訪的機會。而生產隊的一些日常農事活動又沒有什么新聞價值,“巧婦難為無米之炊”,何況我又不是“巧婦”,寫稿這“鍋飯”的確不好做。想來想去,我就看報紙,琢磨人家是怎么寫的。那時生產隊公費訂了各級黨報,隊干部和社員們都不看,一是沒文化,二是沒興趣,有點時間不如去興菜園子或割燒柴,實惠多了。而我卻如獲至寶,一一瀏覽,從報紙上找點子,關起門來寫稿子,寫不出來敲腦子。白天參加生產勞動,是“鋤禾日當午,汗滴禾下土。誰知盤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;夜晚是“寫稿夜正深,汗滴蚊子叮。誰知滿紙文,字字皆苦辛”。盛夏,穿長袖襯衣和厚襪子寫;隆冬,偎在被子里寫,別人吃一種苦,我吃兩種苦:白天勞動,吃體力的苦;夜晚寫作,吃腦力的苦。
稿子寫好了又愁投寄。鄉郵員是隔三差五地才來一次。新聞講時效性,寄慢了就過時了,成了“明日黃花——老了”,寫得再好也不會刊登。所以,由于這些客觀因素,我從1965年秋一直到1970年夏,整整寫了5年,都成了報社編輯部字紙簍里的菜。但是報社的編輯也很負責,即使沒有采用,也是有稿必復,我收到了好多“不擬采用”的“回執單”,成了“退稿專業戶”,幸虧保密工作做得好,沒有被人笑過。編輯同志的回執單都是事先印好的,只須在同志前面填寫一個“王”字就行了。“王同志:感謝您為本報賜稿,經研究,不擬采用,望繼續努力。此致敬禮”。后來可能被我鍥而不舍的精神所打動,回執單再也不是鉛印的了,而是編輯同志的親筆信,并寄上一大摞采訪本、寫稿紙和學習資料,我用香煙盒寫過稿紙寄報社。記得有一次,我們合興公社年輕的團委書記吳昌俊(后曾任公安特派員、京山縣交警大隊教導員)到宋河區開會時,見到辦公桌上有一個很大的《湖北日報》專用信封,上面寫的是“京山縣宋河區合興公社九星大隊四生產隊王章一同志收”。拿過來一看,已被拆開,里面空空如也。他就把這個空信封拿回來,又專程送到我的手上,說,我見這信是寄給你的,早已被人拆開了,里面寄的什么也不知道。我拿回來給你,是不辜負人家報社的一片心意。我被吳書記愛民如子的精神深深感動,再三表示感謝,并叮囑他保密。
1970年七月尾,快要立秋了,生產隊搶插晚稻,正逢大旱,山洼里還有幾畝田無水插秧。生產隊長花錢請來三臺抽水機和師傅,從幾里路遠的小河里三級提水到山上。沿途的通水渠道,就把各家的門板卸下來搭“天橋”,用塑料薄膜鋪在門板上,場景十分壯觀。我覺得是難得好素材!苦于沒有時間寫,白天搭“天橋”,夜晚打早稻,夜晚收工后準備寫,誰知民兵排長又安排我到河邊照抽水機。人也非常困,就想放棄,但夜晚在禾場打谷時,見我的堂弟王章斌從宋河糧管所回來,給他父親打了幾斤糧食酒讓他父親過忙月,第二天就要趕回單位上班。我想這是一個天賜的好機會。半夜收工后,我立即寫好稿子交給堂弟,然后才去照夜。當時我寫的題目是:毛澤東思想閃金光,晚稻不插“八一秧”。正文的導語是:驕陽似火,炎風燙人。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京山縣合興公社九星大隊四小隊干部群眾,三級提水架“天橋”,搶插晚稻不動搖。誰知沒過幾天,稿子被《荊州報》刊登了,還加了“編后語”。因為當時家家都訂有《荊州報》,不等報社寄樣報來我就知道了。盡管一沒署名(署的是隊通訊組),二沒稿酬,我還是很高興,寫了5年的文字終于變成鉛字了!人們都不知道是我寫的,公社干部還以為是下鄉知青寫的,到處打聽作者是誰。吳昌俊書記泄了密,說,可能是王章一寫的,我跟他送過報社寄的空信封。后來我的業余文學創作也實現了“零的突破”,第一篇小說《一筒對節樹》被河北省滄州市《無名文學》刊登了,楊集區一位叫高天然(后曾任縣財政局工會主席)的文學創作者專門跟我送了幾筒對節樹,我用它打了一張方桌和8個“排骨”凳子。這可能是我的“稿酬”。
公社、區、縣陸續通知我參加各級舉辦的通訊報道和文藝創作培訓班。為了不讓生產隊阻攔我,公社黨委還減了我們生產隊2名出外工(主要是修水庫)的勞動力,還要生產隊誤工記工,大隊每天發我2角錢的補貼,保證我能隨叫隨到。我由“地下工作者”搖身一變,成了“合法”身份——“農民通訊員”。在全公社全區范圍內暢通無阻了。1975年3月,我正在大隊養豬場喂豬,突然接到區里的電話通知(大隊電話機設在養豬場),要我去參加縣委宣傳部在宋河區舉辦的北片通訊報道培訓班。3月10日我去報到,只見三陽、羅店區各來了一名宣傳干事,宋河區的5個公社各來了一名農民業余通訊員。縣委宣傳部宣傳干事左其義老師講了一天的課。第二天三陽、羅店的宣傳干事回去了,而我們宋河區的5名農民業余通訊員留了下來,左老師叫區委辦公室給我們開了介紹信,叫我們到各公社去采訪幾天后,回區里寫稿。我被安排到蒼臺公社在黨委辦公室一位同志的陪同下,用了三天時間采訪了幾個大隊,回區里寫了一篇通訊《破千年舊俗,立一代新風》,寫的是宋河區聯升大隊(今高家垱村)青年高世貴、左其秀在水利工地舉行婚禮的事。后來被《荊州報》登了,文章最后署名是:區通訊報道培訓班。
一炮打響,炮炮走紅。后來的稿件陸續被各級黨報、電臺采用,有時一篇稿子幾家新聞單位采用。京山人民廣播站幾乎天天都有播送合興公社的報道(那時家家都裝了有線廣播),人們說京山人民廣播站成了“合興人民廣播站”。
真是“人怕出名豬怕壯”。1977年《湖北日報》將一封讀者來信退回石廟大公社黨委處理。其信的內容是告一位在我們生產隊駐隊的公社領導。公社黨委將來信交由我們大隊黨支部處理,要找出寫信告狀的人。當時我在修八字門水庫,擔任石廟團政工員,不知此事,但大隊鬧得滿城風雨。后來才聽大隊會計對我說,大隊干部認為是我寫的,因為只有我在跟上級黨報寫稿。他們拿著那封“讀者來信”在全大隊有文化的人中調查,要大隊會計辨認是不是我的筆跡。大隊會計反復地看了,斬釘截鐵地說:“這不是章一寫的,因他寫的每篇稿子都要我蓋公章,他的筆跡我很熟悉。”雖然最后不了了之,但母親受了一場虛驚,說,娃呃,莫寫了,那報紙上又掃不下糧來,掃不下錢來,還惹些“糊梢”(惹事),跟我老老實實地搞生產,搶工分;有時間就去興菜園子,割燒柴!
我還是堅持寫作,想體現人生的價值,圓我的夢想。我為了安慰母親,盡量減少外出采訪,一心一意搞生產。可是我不外出采訪,卻有人上門送來新聞素材要我“加工”。1980年6月的一天,我正在隊里勞動,宋河區宣傳干事邵英才(曾任合興中學校長、石廟大公社知青辦主任、合興管理區黨總支書記)騎自行車從宋河來找我,說,章一同志,區委昨天開了一個干部大會,參加會議的全體干部震動很大,區委要寫篇報道見報,我就找你來了。我把他帶來的文件看了一下,覺得有新聞價值,不免手又癢了起來,立即寫了一篇報道交給他帶回去。沒過兩天,《湖北日報》刊登了。這年9月,我便招工了,15年的辛苦換來的一頂“農民業余通訊員”的帽子終于被摘掉了。
2023年5月31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