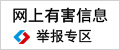老家夏天晚上的熒火蟲、蛙鳴聲、艾蒿薰夜蚊子的裊裊青煙,和禾場東南角老梨樹上的那只老貓,在灣子前面小河經年累月沖刷出的記憶河道里反復泛濫,多虧母親手中那把不知停歇的蒲扇扇出的清涼,才烙出了一線碧綠的記掛。
時間姥姥沉重的腳步剛邁入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那個夏天,參加完高考的我,背上一捆書,右手一袋衣被,還有全班同學無一幸免的疥瘡(俗稱癢瘡)榮歸老家。當母親從我手中接過那袋臟衣被時,我告訴母親我得了傳染性極強的癢瘡,以后我用過的東西要單獨洗,家里人最好不碰,特別是衣服毛巾類。母親說那你先洗個澡,把該換的衣服全換了,我帶你去找鄰村的老中醫看看。洗完澡,看見我端出來的是一大盆血水,母親只說了句苦了我的孩子!就紅著一雙眼睛,不顧酷暑出了門。
母親回家時手里多了一大一小兩個紙包。也不擦擦滿頭的大汗,母親趕緊把大紙包里的草藥倒進做飯的大鐵鍋中,用大半鍋水煎煮。我要幫忙往灶里添柴,母親說這不是你該做的事,你就在一旁等著。那從灶膛里泄出的片片火紅,停在母親臉上的溝壑里,久久不愿離開。母親撩起衣襟下擺抹了一圈,那紅依然懶在原地不走。
在等草藥煎煮的間隙,母親找出一塊四指寬一米多長的木板,擦拭干凈后,和大木盆一起拿進房間。仔細叮囑我,木板要擱在木盆上,先脫光了衣服坐在木板上薰蒸,等水冷了,就坐進木盆清洗皮膚,一直要洗到瘡口發白,不然就沒有效。
你這孩子真是的。母親說,得了病也不早說。剛才我在老中醫那兒才知道,這癢瘡可禍害人了,癢起來一般人是忍受不了的,如果不早治的話,拖下去會要了你的小命!我不以為然的笑了笑,沒您說的那嚴重,何必花冤枉錢找醫生?過些日子就自然好了。
孩子。母親流淚了,只要自己孩子有點么事母親就會流淚。都是媽平時沒能顧上你,讓你受罪了!
按母親說的方法,我足足蒸洗了近二個小時。我以為沒事了,準備出門走走,母親說你別走,我還要給你抹藥。母親手拿小紙包來到房間。快把衣服全脫了,躺在床上別動。我已是快十七歲的大小伙子,還從沒在人前脫光過衣服,我臉一紅,就是不動。母親說你在我面前永遠是個孩子,有么事好怕丑的,快脫。母親突然間威嚴了。我心一震,說那您轉過身去,我才好脫衣服。
母親的手,輕輕的在我身上一個個瘡口點過。每點一個瘡口,一絲灼痛襲來,我沒出聲。但我分明感到,母親的淚水打濕了我每個瘡口上的藥粉。我的淚水也順著眼角,無聲的滴在枕頭上。母親用了一個多小時才點完我的瘡口,那小包藥粉也用完了。
晚飯是母親端到床邊讓我吃的。母親說點了藥不動瘡會好得快。
母親洗過澡,就坐在我床邊的椅子上,手拿蒲扇給我扇涼驅蚊。我有一句沒一句回著母親的問話,迷迷糊糊睡著了。一睜眼,已可見天邊魚肚白的亮光。母親坐在椅子上顯然是睡著的,但手中的蒲扇沒有停!一扇一扇,不緊不慢。我輕輕的坐起來,從母親手中取出蒲扇,給母親打扇。只扇了幾扇,母親就驚醒了。孩子,你感覺怎樣?
含著眼淚,我說,您就這樣坐了一夜?
母親說人老了,覺就少,我沒事。你的瘡口還癢嗎?
我沒有回答母親的話,只是用力的給母親扇風。母親站起身,看樣子草藥還是有效,你再睡睡,我去做早飯了,你自己扇吧。
望著母親的背影,我就想,這草藥和藥粉不會這么神吧,我渾身居然沒了癢的感覺。如果沒有母親深情的淚水,和母親手中蒲扇的涼風,這盤踞半年之久的疥瘡,是不會這么快就走的。三天后瘡痂開始慢慢脫落。
母親雖然離世十多年了,但一看到身上的疤痕,母親手中的那把破舊的老蒲扇,就會在我心里輕輕扇出母愛的芬芳,一直扇到現在,也會一直扇到我和母親相會的日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