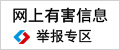似乎每個人的心中總有一處魂牽夢繞的地方,或深或淺,或遠或近。常常聽人談論起一個地方,說那兒有初戀的味道。或許是這句極美的誘惑,心心念念了幾年。雖然每每頷首淺笑,但有絲好奇一直撩撥著,總想去體驗它的神秘。去年幾次想去走走,但都被告之風景已被破壞不值得再去而擱淺。于是,濃郁的遺憾一直在心中嘆息。難道終究成了永遠的缺憾嗎?我忍不住無論如何都要去看看,哪怕失望滿滿。在一個陽光媚好的冬日,風也正好,不早不晚,輕輕地我來了。
或許是傾心的呼喚感應了我的心靈,我迫不及待的向前奔跑。山腳微寒的風肆虐我的衣衫,卻捂不住一顆澎湃的心。沿途的風景在我眼中都只是枯枝敗葉的蕭瑟,怎敵你在我心中的蕩漾。急切的爬過一座座小山,終于見到了你-----梅子凹!
一片片深黃的草浪翻涌,金色的陽光在草叢里跳躍,泛著微微的紅色。那一刻,我怔住了!記憶中從未見過這么茂密又豐腴的草地,密密匝匝,層層疊疊,互不糾纏卻密不可分,隨著坡勢傾瀉而下,匯聚成一道豐潤的瀑布。微風拂來,草莖們輕扭細腰,翩然起舞。草波一起一伏翻騰出漂亮的弧度,身姿愈發優美。突然有些羨慕風這個大自然的演奏家了。驚嘆片刻,忍不住跳進草的懷抱里。躺在你柔軟又寬闊的懷里,恣意聞著獨有的味道,閉目微忖。柔暖的陽光在臉龐打下斑駁的陰影,湛藍的天空飄著一縷縷羽毛般的白云,偶有鳥兒的啁啾傳來。所謂的歲月靜好,莫過于與世無爭的躺在你懷里曬太陽。任調皮的草輕輕的給我掏耳朵,撓我癢癢,讓我咯咯笑不停。哪怕我恣意打滾撒嬌,弄疼了它的肌膚,弄皺了它的衣衫,它依然含笑脈脈,任由我任性得像孩子。
托腮坐在山頂,不遠處,偉岸的梅子凹大橋橫跨兩座山間,橋下流水潺潺。陽光在草浪上撒下無數晶瑩剔透的玻璃珠,泛著七彩的光。忍不住想去摘,可它卻又調皮的在我手掌蕩秋千。恍惚間,似乎置身在大漠,在沙塵里沐浴,茫茫無邊際。仿佛看見一行騎在駝峰的商隊,聽見陣陣駝鈴聲在絲綢之路清脆歡歌。鐵馬金戈玉騎惹一地大漠飛沙,一任孤煙絕塵去。干涸的嘴唇訴說著對綠洲的思念。想起你送我的那壺如甘飴的水。異域色彩斑斕的絲巾裹住疲憊的臉,任垂下的絲幔在沙漠自由飛翔。你輕輕的撩起凝望,我羞澀的轉過身,一任胭脂染上頰。是楚楚動人的眸子溫柔了等待?還是你運籌帷幄的氣魄震撼了心靈?透過一地枯黃,我想到了雪,似乎看見你身披雪衣的身影。密密雪粒一點點覆蓋你的本色,只剩下皚皚的白。雪花片片,輕盈的停憩在你身上,即使層層負重,你也沒嫌棄它變成了胖子。總是忍不住掬一捧雪,當作白糖細細品味。白色,永遠是你心底的顏色,純潔,無瑕,一如你單純的心事。把自己拓印在雪上,聽山雀啁啾而過,想起了泰戈爾的那句:“天空沒有翅膀的痕跡,但鳥兒已飛過。”待到雪融時,復制的我必然會沒了痕跡,但你卻不知道,我偷偷的把一塊紅手帕塞進了你的衣襟。
又似乎望見春天的觸覺。我想穿過冬天去春天看你。細雨迷蒙,你濃密的發際泛起氤氳,碎碎的雨珠在發梢瞬間凝聚滑落,來不及捧起的惆悵,在江南煙雨里一圈一圈漾開,填滿淺淺的酒窩。掬一捧相思,遙寄漸遠的紙鳶。遠山含黛,連綿冗長,似這纏綿的雨絲,纏繞成解不開的心事。你調皮的彈了一滴雨珠漫過我的眼角,我來不及感受冰涼,你溫柔的拭去,輕輕地抻開我微蹙的眉頭。我笑了,你卻心疼的淚盈盈。春雷轟鳴,我如受嚇的小鹿鉆進你懷里,任你濡濕的發梢漸浸衣衫。細看你半黃半綠的容顏在雨里愈發動容。待到春意盎然時,想象你蔥郁的樣子,定是無數次勾勒的草原。清晨我和你策鞭騎行的馬蹄聲驚醒了一地露珠,它們驚惶的模樣真可愛。我撲哧笑了。
笑聲驚醒了我。原來是南柯一夢,不過是打了一個盹!站起來環望找尋同伴們,驀然發現逶迤的山脊是你強有力的脊椎,突兀的石塊是你強壯的骨骼,點綴的松樹是你發達的胸肌,茂密的草叢是你的發際,橋下清澈的水流一定是你清澈的眼眸。不敢回頭與你灼灼的眼神相遇。原諒我的膽怯,懼怕蛇蟲不敢在春天來看你,只能在秋天或冬天演繹與你重逢。雖然你的青春我來不及參與,只能想象你曾經的活力,但這份經歲月沉淀的滄桑美,正是生命真實的演變。誰不是由郁郁蔥蔥過渡到枯黃葉落?一歲一枯榮,野火燒不盡。短暫的枯萎蓄集著蓬勃的綠意,遇見合適的陽光雨露,必然織成厚厚的綠毯。期翼又遺憾著。或許正是這份缺憾美,成了我粉紅的記憶。百般不舍與眷戀凝聚成一個美好的愿望:好想和你搭座草房子!